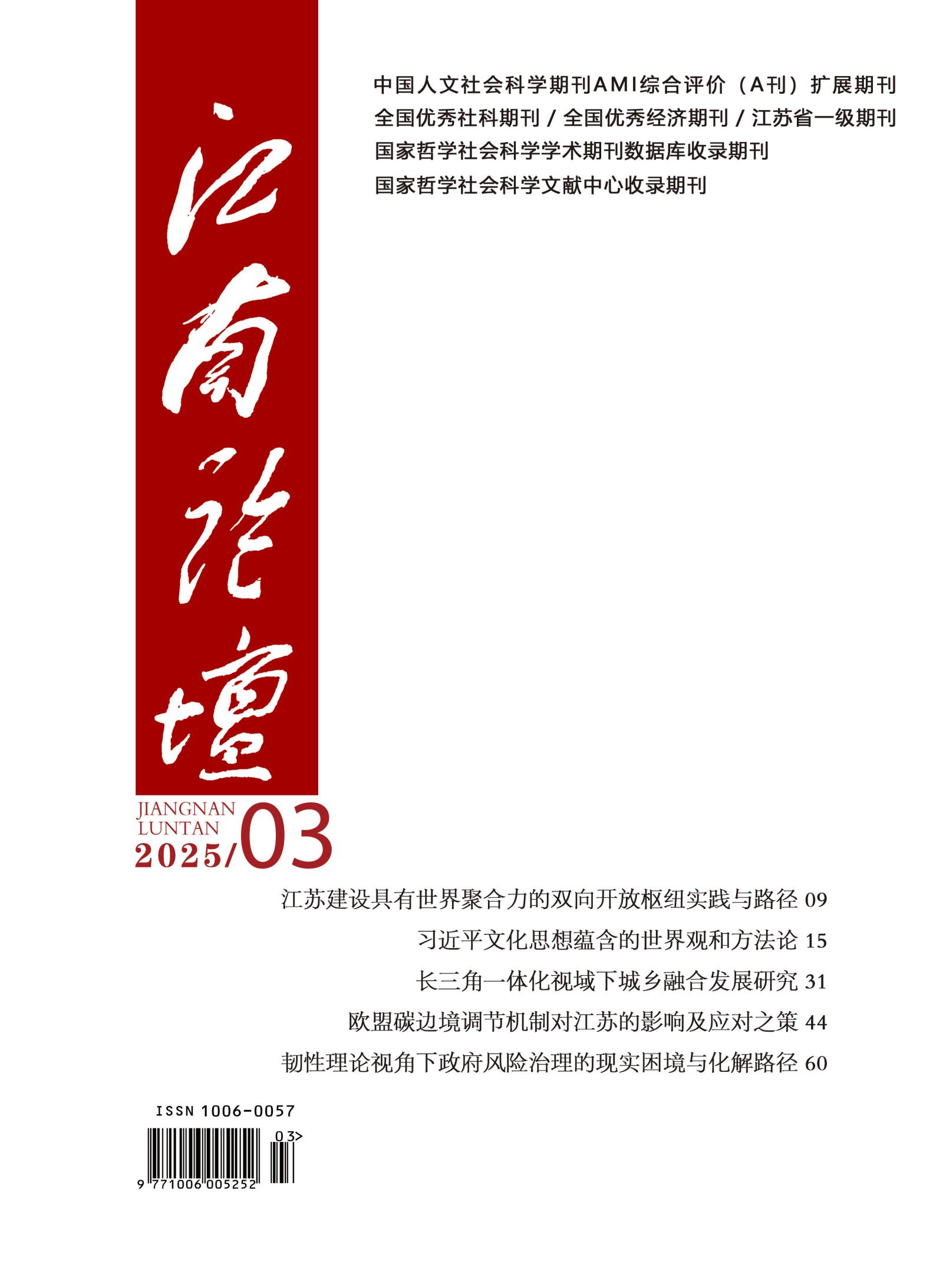清前中期的盐商贸易与扬州文化建设
摘 要 清代前中期,得益于地域优势与政商关系,以扬州为集散中心的淮南盐商势力持续壮大,至康乾时期,其财富、民望、社会地位发展至顶峰,成为极具代表性与极强地方色彩的江淮新兴力量。扬州盐商恤灶体民、义利并重,拥有政府授予的绝对垄断经营权,多数重文崇儒、喜好奢华,广泛寻求“贾而儒”之途径,以其强大社会影响力与雄厚资金实力推动了江淮两岸城市风貌的发展、转型及定型,共同铸就“海内文士,半集淮扬”的历史盛况。综清一朝,两淮盐商对淮扬文化的兴起、地方商业经济的繁荣以及扬州城市文化建设作出了相当的价值贡献。
关键词 扬州盐商;城市建设;书画;饮食;扬州文化
扬州盐商又称两淮盐商,是指侨寓于扬州从事盐业的各地商人,多来自于徽、晋、陕、浙等多个地域性商帮。清中叶为扬州盐商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康乾盛世下,盐商团体好学博古,以兴学、助学等出力扬州文化教育的事迹屡见不鲜,亦有官、士、商群体的身份互动,一时出现士商“异业而道同”的现象。二十世纪始,学界之于清代两淮盐业与扬州盐商研述颇多,亦多有著作出版,对清代江淮盐商家族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探讨。本文聚焦康乾时期的扬州文化教育事业,对行进至清代前中期、发展至鼎盛的扬州盐商,之于扬州城市文化的重要贡献、世风构塑等作出论述。
一、明清盐政转型与两淮盐商贸易
在中国古典社会结构中,社会分类以儒家思想所设的理想社会结构为基础。在传统农业经济社会中,商人阶层的社会活动和区域流动性较大,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多实行限商、抑商及相关制约政策。盐政经贸事业高度关系中古国家发展及社会稳定,唐肃宗时制定盐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1]安史之乱后,刘晏改革盐法,令“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2]榷盐法规定盐商在盐司纳榷取盐后,在转卖过程中不再加税。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持续迸发,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社会逐渐向近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变革,[3]以士、农、工、商为基础的四民关系开始动摇,传统社会秩序有所变动,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
明朝前中期,政府以盐固边,向运送粮食至北部边关的商人发放盐引,并分放特权。山西、陕西商人集团聚居于扬州最为繁盛的下关,亦多有徽商大量涌入扬州、淮安等地,经商、兴业、定居于此,以民利垄断民间食盐。明中叶后,“开中法”废弛,政府实行“折色制”,国家立纲法,规定商人以纳银代替纳粮。“折色制”之施行引发了徽商的兴盛,拥有盐引的商人凭借地域差价行盐纳课,通过盐引换取食盐利润;至明后期,政府以引窝为据,商人无需分赴北境贸易往来,便可获取食盐运销特权。
清初,受制于朝代更迭与弥久战乱,全国农、工、商等各行业遭受波及,两淮城市经济萧条,盐商利益损失惨重。平定三藩后,政府以“恤商裕课”为核心政策,对盐商课以较轻的盐税,并以食盐专卖作为获取财政收入的直接手段,同时招贩行票,规定盐商须先向盐运司交纳盐课、向国库缴纳银两,以直接的白银便可购得盐引。“两淮之盐法定,而天下之盐法准此矣”,[4]清政府食盐运销体制采取“引岸制”,向盐商划分贸易区域,编立纲册、分配并分割食盐销售市场,扶持并复苏盐业经济。“纲法始定”下,政府规定盐商需向盐运司交纳盐课、领取盐引,至指定产区向灶户买盐,并在指定地点与口岸进行食盐销售。[5]
二、清代的两淮地方与扬州盐商
十八世纪为中国君主专制的全盛时期,江南商业城市密集出现,全国亦出现大商帮,人口渐趋突破四亿。扬州地当要冲,为全国最重要的产盐区,其城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情状与中国古代盐业及漕运事业高度相关。扬州水陆交通发达,自京杭大运河开凿至元代,即为两淮盐业商贸重镇;在全国盐场中,两淮盐场占地面积大、课税重、行销地域广、报效银两多。康乾时期,中国农业与商品经济发达,国家盐业、盐运机制完备,此时两淮盐业发展最为鼎盛。得益于运河物流与盐业经济,清代扬州逐步成为江淮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得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纲法制下,淮盐贸易及盐业经营体制渐发生根本性变革,部分商帮垄断食盐贸易,商人承包并转包食盐销售,新型政商关系逐步形成,两淮盐商渐成为全国商界巨擘。
在地理位置上,大运河贯穿长江、黄河、淮河、海河与钱塘江,扬州贯穿南北东西,为江淮地域贸易中心,往来交通便利。作为水陆交通枢纽,扬州临近淮河两岸、全国最大的产盐区,并设有国家盐业垄断管理机构——两淮盐运使司。江淮地域为中国古代重要海盐产地,河道通畅,渔网密集。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点,得水陆交通及漕运之便,又与江南金陵、浙江富庶地区一衣带水,与长江下游一带重要地方存在频繁经济往来,地域风俗文化连结紧密。
得益于清代两淮盐务中的引窝制以及围绕其交易、炒作、质押而形成的规模庞大的资本市场,[6]两淮食盐专卖制承明后期之专商世袭卖引纲法,扬州盐商独占长江流域及江淮平原的多数食盐消费市场,盐业渐成为两淮集聚程度最高的商业贸易之一。清代前中期,江淮社会相对稳定,地方盐务、盐运与漕运系统趋于成熟,市镇体系完备,江淮盐场的盐通过扬州盐商运输,进入长江辐射供应的数个周边省份,获利巨大。兼有康乾时人口增长、淮盐运销市场扩张、海盐生产技术提升等社会因素,以徽商为主体的各地盐商巨贾云集、建业于此。扬州盐商勤勉智慧、恤灶体民,同时经商重文,进取而致富,兼合江淮风俗、扬州本土文化与徽商客商文化,扬州亦成为清代两淮地区最为繁盛兴荣的盐业运输中心。
在国家南北商业往来中,徽商因国家盐业经营体制之变革,渐成为经营淮盐和浙盐的主要力量,[7]并于清初形成垄断。徽商向盐运使衙门缴纳盐课银,购得盐引后,通过半垄断民间食盐,将大额民间用盐需求通过盐引贸易进行利润流转,再收获差价,将盐业所得的大额赋税重新折算成为白银缴纳,获取新的盐引与利润差价。扬州盐商获利甚丰,渐发家于此,成为声名显赫的一方望族。扬州盐商分为窝商、运商、场商和总商四个名目,各行其职,亦有徽州大族迁居于此,聚集家族财富,在往来贸易中攀附官府、寻租皇权,从悬殊极大的购销差价中获取丰厚财富,又借官府特权,攫取巨额商业垄断利润。
清代,两淮盐课分为商课、灶课。商课征于盐商,按承销盐引数量计征;灶课征于灶户,按所占草荡面积计征。[8]清时“纲商引岸”制高度垄断食盐贸易,在攫取巨额利润的盐商团体之外,清政府亦需盐商“报效捐”,地方政府对扬州盐商收取足量的赋税,从盐业中获取高额盐课税收充作财政收入。江苏淮盐质优利厚,销区广、产销量大,康乾盛世下,人口稠密,江淮盐课有“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之称,[9]清乾隆嘉庆间达7800万两,与同期国库存银相当。扬州盐商辖区宽广,占享地理优势,同时输纳巨额,大量白银涌向军饷、慈善、朝贡、工程、庆典等社会渠道,[10]有“豪侈甲天下”“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之说。[11]江淮一带有江春、黄履暹、卢绍绪、程之歆、汪应庚、汪廷璋等从事盐业,或为大盐商,或为大盐官,凭借食盐利润占据巨额社会财富,逐渐累资巨万。从官专卖,至官商共营,到商专卖,清代盐政事业趋向于官商一体化,有“官商”身份与官僚支持的扬州盐商大量以盐改籍,盐册占籍,“占籍”于淮扬;财富聚集之下,渐成为清代富甲一方的地方群体,财力雄厚,鼎盛一时。
三、崇儒之道:教育引领与人文建设
盐商群体发迹后,对文人的礼遇与实质性支持渐形成清时江淮商人崇文、文人议文攀商的特殊士商模式,有力推动了扬州文化、教育、慈善事业发展。清前期,社会经济逐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淮盐的顺利销售、两淮盐商之繁盛极大地促进了扬州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康乾时期,扬州文儒荟萃,地方人文素养浓厚,扬州文人与以徽商为主体的儒商家族交往频繁,这一时期,扬州地区士商、政商关系均较密切和复杂。
对于扬州盐商,食盐利益中赚取的大量财富得益于与官府稳定的盐引交换,其对民间食盐的半垄断商业特权来自于清中央与地方政府,丰厚的食盐课税之下,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皇商”性质。扬州盐商客籍淮南,数代世袭扬州,群体声誉、名望、社会评价较为突出。此时,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亦发生转变。两淮官商汇聚,盐商团体存在有“由商入仕”等社会现象,三百余盐商家庭通过捐官,或“学而优则仕”入仕,读书业儒、致力培养后代之仕进,通过学术、科举从政,而后实现功名。两淮盐商集团崇儒情结强烈,与儒学士人多有互动,有士商混而不分、先商而后仕现象。文人学士的价值观念,如义利观念、士商等级观念等亦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士商阶层交往、融通、流动甚密,[12]盐商与江淮文儒团体亦“以商重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商而兼士、贾儒结合,迭相为用,加固自身与官僚的政商关系。[13]特殊政商关系下,扬州盐商顺应地方民心与官僚认可,对教育文化事业的鼎力协助,引领了近两个多世纪的扬州社会文化风向,对江淮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较于中国古代的传统商人团体,扬州盐商“自附于风雅”,自身贾而好儒,亦多修身、治学,涵博多才、审美雅致,同时,更具强烈的社会责任、民生担当与道德准则。殷实的经济实力、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滋养了淮扬盐商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担当精神。[14]十八世纪,扬州政治环境平稳,经济社会发达,士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两淮教育、公益、文化、艺术及慈善事业在扬州盐商的鼎力帮扶与慷慨物资投入下发展昌盛。得益于儒家重礼节、伦理的传统文化信仰,盐商团体务盐筴于淮扬,广交名士,积极捐资兴办学宫、出资兴建书院,为地方文化传承与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亦与慕名来扬的各地文人交流,吸引大量财力雄厚者捐建、捐资;扬州盐商重文教、爱惜人才,刘声木《苌楚斋三笔·教义学者绝后》有:“向由盐运使署领给官款,修脯所人甚丰,寒士每费尽心。”[15]
扬州书院的建立与发展,部分得益于盐官与盐商的资金筹措。康熙时,安定书院是盐商等为祀奉宋儒胡瑗所筹建,朝廷监察御史来此巡视两淮盐政,为书院题写“安定”院额。在盐商群体捐资助教的直接经济支持下,义学事业在扬州兴盛发达,学者文人汇集、文风暇畅,学术氛围浓厚,人口流动往来频繁。扬州书院膏火丰厚,“皆隶于盐官,藉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才之地”。[16]出于对传统儒学与文儒士人的尊重,两淮盐商聘请名师、延揽学者、为书生出资膏火费以供其生计,揽才、引才、养才、济才,扬州书院于清代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扬州画舫录》载有“敬亭书院在北桥,建于康熙二十二年,两淮商人创始,因御史裘充美论湖口税商疏,感其德建此,令士子诵读其中,京口张九徵为记”等。[17]盐商群体热衷文化事业,后陆续筹建有敬亭书院、江甘学宫,大盐商马曰琯重修梅花书院,并珍藏典籍于其中。盐商群体捐资兴教,世人崇文重教,名师硕儒外来频繁。书院文化之繁盛推动了学术交流与扬州学派的形成与壮大,民间崇儒尚贾之风厚重,地区教育水平逐步提高、科举繁盛,形成了良好的学风与社会风貌。阮元《重修扬州会馆碑铭》有:“维我广陵,元甲天下,能领江乡。”[18]
四、儒商典范:艺术传承与民风塑造
扬州城兴于两淮盐政,发达的经济社会推动了扬州上层建筑昌盛发展,盐商托名风雅,品第不俗,广交天下名士,将大额财富投入扬州文化教育与艺术投资行业。清代两淮教育、戏曲、学术、审美、艺术事业等皆与扬州盐商的风潮引领、经济帮扶直接相关。盐商家族亦商亦儒,极富雅趣,自身重视文化科举,凡事务求精致,亦大兴笔墨文艺,出资建书楼、广藏书、收藏古玩字画、蓄养伶人、竞蓄书画图器、刊刻贮藏图书等。在儒文化影响下,盐商踊跃捐输,在具社会意义的公益建设如助修书院、修筑水利道路、赈灾、抚恤等地方社会性事业方面作出大量贡献。
清代扬州盐商与文人活动频繁。清乾隆年间,不同阶层的盐商、官僚、文士等齐聚大盐商“扬州二马”(马曰琯、马曰璐)所建藏书楼“小玲珑山馆”与马曰琯行庵,约四十余人共成韩(邗)江吟社。韩江吟社由“扬州二马”主持,频繁举办诗文集会,为清中期广陵诗坛最引人瞩目的文学盛事。扬州盐商重金组织艺文活动,雅集前后共举行近百次。两淮盐商外,多有著名学者、诗词大家、画坛怪杰、漂泊寒士、迁客谪臣等云集,另有虹桥修禊活动,名人酬唱,觞咏为乐。韩江吟社留下诗歌近700篇,唱和之作汇为《韩江雅集》,由二马兄弟出资刊刻。“扬州二马”亦热心文化教育事业,出资重修书院、广藏书籍,“倾接文儒喜交久敬”“一时文宴盛于江南”。
康乾时期的扬州吸引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驻足于此,优秀的文人画家,如“扬州八怪”的盛名也得益于扬州盐商的实质扶持与地方繁荣昌盛的文化市场。“扬州八怪”由繁盛的扬州文化吸引,自各地分赴来扬,得盐商赞助款待。“扬州八怪”个性鲜明,品格独特,艺术内涵丰富,定居后在此以画寄情,成就一番艺术名望。盛清时期的淮扬地区人文渊薮,诗人、画家、雅客云集,文士商人宴饮唱和,盐商群体养蓄家班、建立戏院,重金聘请名旦名角以招待客商、官员与士绅。“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19]南北曲剧名流汇聚,戏剧曲艺业兴盛,“伶优杂剧歌舞吹弹各献伎于堂庑之下”,[20]促进了中国戏曲事业的发展。盐商喜好收藏书法字画,其所偏爱戏曲表演、玉器漆器、园林建筑等亦得兴盛繁荣,形成清代两淮文化艺术领域的顶峰。
不同于苏州园林,扬州园林数量多、构造精,豪放与婉约并蓄,兼容南北审美之大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中极具地方特色的象征性建筑。扬州盐商、文儒群体亦以文化园林为平台,展开大量文化交流活动,宴饮宾客、赏景赋诗、欣赏戏曲或行诗文之会。被誉为“晚清第一园”的何园与个园,即为清时扬州城富甲一方的大盐商故居。清代盐商著名园林中,另有江春的净香园和康山别业,黄履暹的趣园,马曰琯、马曰璐的小玲珑山馆,洪征治的大洪园和小洪园,汪玉枢的九峰园,[21]均作为扬州园林的代表。清代扬州园林融合地域特色,采取自然景观与自然法,有不同于传统园林的廊道建筑,形成中国园林中风格迥异的山水景观。“扬州以园亭胜”,[22]扬州园林文化于清代的鼎盛,与两淮盐业经济密切相关。
《扬州画舫录》为李斗居扬州时,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之实录,多载有当时扬州园亭奇观、人文奇士社会生活,笔记条目清晰,对扬州盐商奢靡消费风气描述详尽。《扬州画舫录·盐商富态》中载有“初,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概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掌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23]盐商家族风尚侈靡,置办家宴、招待宾客均承奢靡精致之风,菜肴新奇、食具华美。淮扬菜系盛于明清,选料严谨、因材施艺。淮扬菜的流播、发展与明清盐商饮食喜好高度相关。清代,扬州餐饮业发展兴盛,茶楼酒肆繁多;淮扬菜系精于烹饪,强调食材的新鲜与细腻复杂的工艺技术,将普通食材精雕细琢。盛清时,盐商附庸风雅,风流宴饮,也为攀附官威,笼络人心,将别样的消费格局发展为上层社会内部的社交手段,淮扬菜狮子头、蟹黄汤包、生肉藕合、江鱼宴等食材精细、制作刀工精美。清代盐业经济下,扬州城消费发达、众多行业兴起,第三产业领域如沐浴业、按摩业、理发业、香料制品、印刷行业在民间发展各具特色,渐形成了“慢”生活的社会文化特质。盐业的发达进一步促成扬州消费市场、两淮商业领域的繁荣与外部人员集聚,形成了扬州特有的社会群体结构与文化市场。
参考文献:
[1]董诰.全唐文:第670卷,第7部[M].北京:中华书局,1983:6826.
[2]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2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6:7286.
[3]汪崇筼.一个中国商品经济社会萌芽的典型——论明清淮盐经营与徽商[J].盐业史研究,2008(4):3-18.
[4]吉庆,王世球.乾隆两淮盐法志[M].乾隆十三年刊本:3.
[5]何炳棣,巫仁恕.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02):59-76.
[6]余康.清代两淮盐务中的引窝资本市场[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06):67-83.
[7][12][13][14]司志敏.文化自觉与社会担当——扬州盐商对书院教育发展的贡献研究[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35(11):21-30.
[8]穆家良.两淮盐业的历史脉络和深远影响[J].江苏地方志,2023(06):4-9.
[9]佶山,单渠.嘉庆两淮盐法志:第55卷[M].同治九年扬州书局重刊:1.
[10]王宁宁.商儒相济:清代扬州盐商的文化角色[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8(04):8-11.
[11]李澄.淮鹾备要:第7卷[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419.
[15]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三笔: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8:540.
[16]吴锡麒.曾都转校士记,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第19卷[M].嘉庆十五年(1810)刊本:9.
[17][19][22][23]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7:20,65,89,77.
[18]阮元.揅经室集·四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3:735.
[20]阿克当阿.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第60卷[M].嘉庆十五年(1810)刊本:8.
[21]吴海波.清代两淮盐商的艺术贡献[J].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9(02):339-346.
本文系2021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文化+历史视阈下的《古代工艺美术史》教学模式改革”(编号J2021566)的阶段性成果。
(刘心怡 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张清文系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