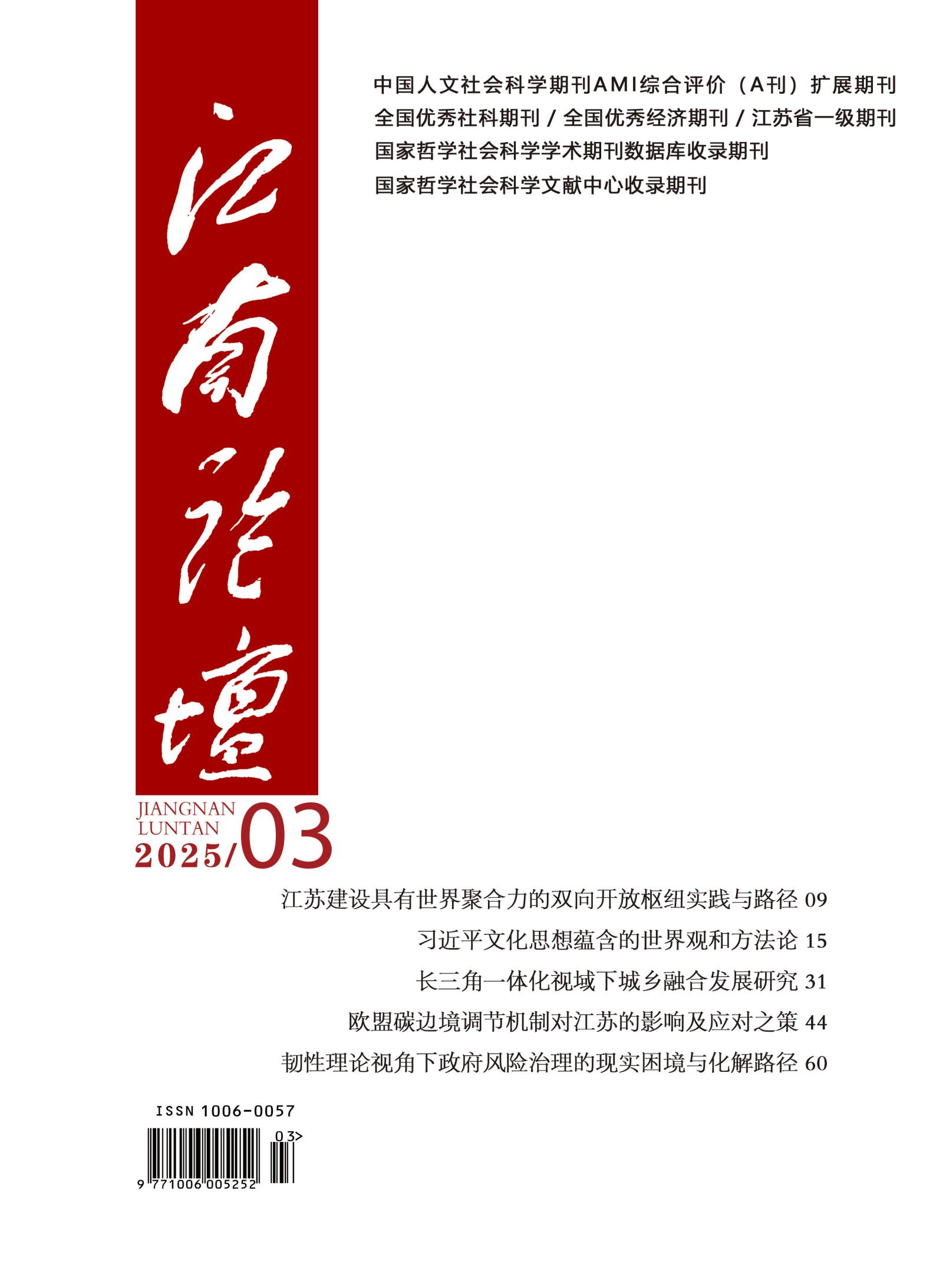“中之人”的数字进化与真我异化
摘 要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劳动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和平台,使其能够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创作和互动。以“中之人”为代表的虚拟主播与偶像行业,通过“皮套”与“动作捕捉”等数字技术,以“二次元”虚拟形象与观众互动,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数字劳动形式。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中之人”这一新型劳动形式的“数字进化”特征及其背后暗含的“真我异化”现象进行辩证分析,揭示其中蕴含的资本新型剥削方式,从而为数字时代劳动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关键词 “中之人”;虚拟主播与偶像行业;异化劳动理论
引言
在技术进步和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兴的劳动形态,已逐渐成为当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劳动涵盖内容创作、数据处理以及虚拟产业等多个领域,其中,“中之人”作为虚拟产业的典型职业代表,依托数字技术的进步,为诸多劳动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形式和机遇,展示了数字劳动丰富的价值内涵。然而,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深化发展,“中之人”的劳动过程日益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并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劳动异化的新型特质。为此,如何辩证地看待数字劳动的进化与异化,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当前,“中之人”已经成为传播学、经济学、人机交互、伦理学以及美学等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对象,但是尤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深层解读。基于此,本文聚焦“中之人”数字劳动的新特征,并以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石,深入剖析其背后隐匿的异化现象,揭示数字劳动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剥削本质。此研究对于深化数字经济劳动关系的理解、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导向、激发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积极作用以及防范技术异化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何为“中之人”:虚拟与现实交汇的关键角色
“中之人”源于日语“中の人”,直译为“里边的人”。“中之人”起初指代布偶服装之下的扮演者,他们身穿“皮套”外衣(如卡通形象、地方吉祥物的外壳),通过肢体语言和舞蹈表演的形式来赋予布偶“皮套”生命力。由于布偶“皮套”IP名气的提升,“中之人”逐步踏入影视和广告领域,其职能范围进一步扩展至声优行业。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以及人工智能(AI)领域的快速发展,为“中之人”提供了更加先进的技术支持。他们利用“虚拟皮套形象的外壳”与“动作、面部捕捉技术”,成功地将个人魅力与虚拟形象融为一体。在直播行业的助力下,“中之人”以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的形式迅速崛起。2016年,日本虚拟偶像兼主播“绊爱”(Kizuna AI)的出现,使“中之人”迎来了事业高潮。至此,“中之人”这一概念从现实彻底转移至虚拟世界,指代通过数字技术(如动作捕捉、语音配音等)操控虚拟形象的幕后真人创作者。
二、何以进化:“中之人”数字劳动新型演化的特征
(一)理想自我呈现:数字技术与人设符号的完美交融
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行业置身于多元文化交融的领域,涵盖了二次元、粉丝经济和网络直播等多种亚文化,呈现出相互交织、共同发展的态势。在国内,“中之人”主要在“哔哩哔哩”平台的亚文化圈集结,其“皮套”设计往往二次元风格浓烈,如“大眼萌妹”“银发猫耳”和“少男少女”等。同时,部分形象融入了本土“国风”特质,主要为“汉服”“异域”以及“宗门修仙”等设计元素。
具体来说,“皮套”作为“中之人”向观众呈现的第一印象,不仅体现了个人风格,还巧妙地迎合了受众的审美需求。由于“皮套”所代表的虚拟形象与“中之人”的真实性别可以不一致,因此“中之人”有充足的创作空间,展现个人趋于完美又符合理想的虚拟外观。[1]通过细致入微的样貌设计、场景构建与整体风格布局,“中之人”巧妙传达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趣味,从而成功吸引受众的目光,促使其在直播间驻足。[2]
然而,单凭华丽的“皮套”形象难以持久地俘获观众的心,其背后的“世界观”与“故事情节”需由“中之人”继续填充和完善,即在直播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人格特质,为虚拟形象注入灵魂。这种“人设符号”的设定不仅赋予虚拟角色鲜明的身份认同,还为内容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世界上第一个虚拟YouTuber“绊爱”为例,她的角色设定是一个具有自主意识的“AI”。这一设定赋予其独特的科技性和未来感,同时也为互动内容制作增添了许多幽默情境。例如,她在视频中经常调侃自己作为“AI”可能会发生系统错误或程序崩溃。这种轻松幽默的表现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与此同时,“绊爱”的性格设定生动鲜明,塑造了一个活泼、开朗,同时带有些许“天然呆”的虚拟角色形象。这种符号化的个性设定,不仅让观众印象深刻,也成为她吸引粉丝的重要特质。此外,她的言谈举止、语气和情感表达经过精心设计,与“AI”身份高度契合。例如,她常说的“我是AI,所以我无所不能!”等台词,不仅体现角色设定的幽默感,还通过符号化的情感表达与观众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共鸣。
如此,在“数字皮套”与“人设符号”的双重加持下,使得“中之人”介于虚拟表象与真实实体之间,其存在形式类似于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千高原》中提出的“无器官的身体”概念,即一种超越了有机体束缚的存在,展现出自由、动态和流动的特质。通过数字技术与人设符号,“中之人”得以在虚拟空间中展现自我,打破现实中的各种限制,为观众带来一场奇幻的视听盛宴。这一职业的数字技术特性,不仅帮助广大劳动者摆脱现实生活中身份、地位等潜在因素的束缚,也规避了“颜值至上”的现实困境。[3]同时,它为社会上的残障群体提供了展示自我和表达个性的机会,提升了边缘化群体在社会中的可见性、话语权和工作机会。[4]
(二)巨额流量变现:粉丝经济与平台机制的协同推进
“中之人”在直播平台的流量变现收益依赖于粉丝经济与平台机制的协同推进,具体如图1所示。粉丝经济是“中之人”收入的核心驱动力,取决于粉丝的忠诚度、参与感和情感连接。“中之人”通过持续的内容输出与粉丝互动,逐渐建立起强大的粉丝群体。这些粉丝不仅观看直播,还通过打赏、购买虚拟礼物和定制弹幕等方式,为其提供经济支持。例如,哔哩哔哩平台上的虚拟主播“泠鸢yousa”,通过定期的音乐直播、翻唱作品以及个性化的互动方式,吸引了大量忠实粉丝。这些粉丝的忠诚度和深度参与为主播实现流量变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粉丝经济的基础上,平台机制助推对“中之人”的流量收益变现起到了关键作用。平台通过流量分发、算法推荐和打赏等手段,助力虚拟主播和偶像扩大影响力并实现商业化。例如,哔哩哔哩的“首页推荐”功能依据用户的观看历史和兴趣偏好,精准推荐虚拟主播的直播或视频内容,从而吸引更多观众。平台还凭借打赏功能和会员订阅服务,与“中之人”形成利益绑定,实现双赢。观众通过购买虚拟礼物进行打赏,平台按比例抽成。会员订阅服务则为粉丝和主播提供了更多特权和福利,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互动和联系。
粉丝经济的多元化变现途径也是“中之人”收入的重要来源。随着虚拟IP影响力的扩大,能够吸引品牌合作,推出联名周边产品,提升品牌曝光度和市场影响力。尤其是哔哩哔哩等平台推出的限量版数字周边产品,如虚拟形象手办、数字艺术品等,进一步丰富了其收入渠道。与此同时,身穿“皮套”的“中之人”不仅在线上具有影响力,线下活动和跨界合作也成为其扩大商业化的重要途径。例如,哔哩哔哩的虚拟主播参与线下的粉丝见面会、音乐会等活动,不仅增强了与粉丝的互动和情感连接,还带来了新的收入来源,并通过拓展商业化空间,逐步形成稳定且多元的经济模式。
综上所述,“中之人”的数据流量收益变现是粉丝经济与平台机制协同推进的结果。粉丝经济通过情感连接深度参与和多元化的支持方式,为虚拟主播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平台机制则通过流量分发打赏功能和会员订阅等手段,帮助其扩大“皮套”人物的影响力并实现商业化。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的拓展,“中之人”将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
三、为何异化:“中之人”数字劳动四重异化的释解
近年来,尽管虚拟主播与偶像行业蓬勃发展,但也频繁出现“休眠”现象,即不再进行直播或其他数字活动。例如,世界知名虚拟主播“绊爱”于2022年2月宣布“无限期休眠”,国内知名虚拟偶像A-SOUL女团成员“珈乐”也于同年5月进入“直播休眠”状态等。这一系列“休眠”引发无数粉丝的愤怒与不舍,而“中之人”随后也相继被爆出遭受“公司的压榨”“高强度劳作”以及“薪资待遇过低”等问题。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左右行业的手”,即掌控行业导向的平台资本,通过榨取回报与身份利用,不断压榨劳动者。为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劳动“异化”,本文结合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四重维度加以阐释。
(一)产品异化:劳动成果与“中之人”相分离
前文阐述“中之人”数字劳动新型演化的特征时,多次提及“皮套”与“算法”等数字技术。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本身并非异化问题的根源,问题在于劳动者对技术的使用方式以及技术被应用的具体情境。从这劳动结果来看,“中之人”利用“皮套”等数字技术所产出的数字劳动产品,如直播内容、互动数据等,通常被数字平台占有和支配。这些劳动成果并不直接归属于劳动者,而是被平台以商品化的形式流通和交换。马克思指出:“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5]这种外化、相异和对立在虚拟主播和偶像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虚拟形象和品牌通常归属于公司或平台,而非“中之人”本身。所以即便是他们通过劳动塑造了虚拟角色的形象和个性,创造了巨大的品牌效应,但其所获得的收益却寥寥无几。这种产品上的异化导致劳动者与自己创造的价值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脱节。此外,由于数字劳动产品的“伪娱乐性”,平台往往会利用“免费”和“无偿”的“诱饵”吸引用户参与。[6]这些用户(包括“中之人”本身)在享受数字娱乐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为平台创造数据价值。这些数据被平台采集并垄断,经过加工后又成为吸引用户二次投入的商品。[7]由于“数字技术的遮蔽性”,“中之人”难以直接感知自己的劳动价值被剥夺。总之,哪怕其是虚拟角色的“灵魂”,也无法完全掌控自己劳动的最终成果,更无法决定虚拟角色的未来发展。
(二)劳动过程异化:“中之人”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丧失
“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8]“中之人”劳动产品的异化,必然体现在其劳动过程之中。劳动过程的异化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失去了对自己劳动的控制,劳动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活动。从表面来看,虚拟主播由“中之人”进行自由操作,但实际的工作内容和表演形式往往受到平台规则、公司要求和市场导向的严格制约。例如,他们须遵循背后团队编排的脚本、既定的直播频次以及规定的互动模式展开表演,导致自主性与创新空间显著受限。在劳动过程中,“中之人”被外部因素(资本主体、市场需求)所支配,难以掌控自身的劳动进程。此外,由于行业竞争激烈,他们需要完成长时间直播任务和高频率互动,以维系虚拟角色热度及粉丝关注度。与此同时,平台和企业秉持优绩理念,将追求极致运营效率的精益思维转化为严格的控制机制。这在“中之人”的劳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虽然在屏幕前其所呈现的是自由的虚拟场所和梦幻表演,但劳动实际是在被监控的环境中进行。他们所展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记录和评判,并以工具化和精确的方式被资本衡量其所蕴含的劳动价值和潜在收益。在这样的高压工作环境中,“中之人”不得不迎合外部标准,努力维系流量推送和虚拟角色的市场价值,从而深陷资本逻辑的规训,加剧了行业内卷。劳动逐渐变得单调、重复且充满压力,其劳动兴趣和热情逐步消退,劳动最终沦为一种无奈之举。即便劳动应该是属于劳动者即“中之人”自己的生命实现的主体性活动,但它却异化为属于他人发家致富的他性活动,即“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9]
(三)自身异化:“中之人”与其内在的类本质相疏远
马克思在探讨异化劳动时指出,劳动产品与劳动过程的异化进一步导致劳动者与自身类本质的疏离。人的类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劳动”,它不仅赋予生命创造的力量,还将人类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本质得以展现,人们因此体验到深刻的幸福感。然而,在资本逻辑的私有规训下,劳动发生异化,剥夺了人们原本的幸福感。
具体从“中之人”长期扮演虚拟角色的劳动中来看。首先,表现在劳动主体的虚化。在数字劳动中,“中之人”感受到自己只是平台运营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在劳动过程中被平台严格规划和支配,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这种主体性的虚化使其难以发挥自身潜力,也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其次,体现在情感劳动的消耗。“中之人”不仅是技术的操作者,还需通过虚拟形象与观众进行情感的互动。有时为了迎合观众的需求和市场的期待,需表现出与自己真实情感不符的状态,甚至以夸张和虚伪的方式回应粉丝,而长期的情感劳动会不断导致并加剧其情感耗竭。[10]最后,呈现在自我认同的双重危机。长期沉浸在虚拟世界中,“中之人”不但可能会产生自我与角色的认知混乱,而且其虚拟角色的成功并没有为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应的回报或认可。究其原因是虚拟主播与偶像行业为了维持虚拟角色的神秘感和吸引力,选择不公开“中之人”的真实身份。其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的认同感和成就感与现实生活中的默默无闻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身份的隐匿性可能导致“中之人”感到与现实社会的疏离,他们的劳动成果无法直接与现实生活中的身份相连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自我认同的困惑。
由此,劳动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与意义,仅沦为人们谋生的手段。“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11]异化劳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与人的类本质之间的疏远与对立。
(四)社会关系异化:“中之人”与他人间的普遍疏离与对立
马克思强调,“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2]过去,异化劳动不仅加剧了工人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诱发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与竞争。如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具体表现为个体间为了最大化的自身利益而广泛形成的对立态势,甚至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人际交往之中,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疏离感与对立状态。
首先,表现在“中之人”虚拟互动的浅层化。其与观众的互动主要通过虚拟角色和数字平台进行,虽然这种互动在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频繁和紧密,但实际上,此类关系往往是浅层次的、虚拟的。他们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更多是建立在商业化的基础上,缺乏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虚拟互动虽然看似热闹,但在本质上是商品化、工具化。
其次,表现在“中之人”与团队关系的疏离。在幕后工作流程中,“中之人”仅是团队中的一环,他们的劳动被分割成不同环节,如技术团队负责虚拟形象的设计,市场团队负责推广等。“中之人”与其他团队成员间的劳动缺乏直接的联系,他们可能与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劳动者产生疏离感,难以形成真正的合作和交流。
最后,表现在“中之人”与平台劳动关系的弱联系性。由于“皮套”“直播交互”以及“动作捕捉”等简单的数字技术皆被资本所垄断,“中之人”一旦脱离这些设备便无法实现,其深陷技术强权引发的人的异化与社会危机即“技术利维坦”的胁迫。因此,这种不对等的劳资关系往往呈现出弱联系性的特点,平台通过算法机制评估“中之人”的劳动价值,又以技术垄断的劳资合同对其进行管理和约束。这一背后深切地暗含着“中之人”的劳动权益无法得到强有力的保障,甚至是“皮套”之下可被任意替换的“白鼠”,劳动背后缺乏足够的人文关怀和职业发展前景。这种弱联系性使得“中之人”难以形成对平台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结语
随着科技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愈发凸显,“中之人”实现了职业生涯的“数字进化”,然而其劳动价值却时常遭受资本剥削,并在劳动过程中深受资本的规训,诱发“真我异化”。这种异化现象不仅揭示了数字时代劳资关系的异化问题,更展示了数字劳动者的现实困境。为此,必须重视“技术利维坦”等技术强权所诱发的一系列后果。不断加强立法和政策手段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保护数字劳动者的权益。同时,扬弃科学技术异化,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技术的普惠应用,减少技术异化现象。此外,深入剖析和变革劳动关系,推动建立公平、透明的收益分配机制,确保“中之人”的劳动价值得到合理回报。致力于在数字经济领域内构建更加公平且人性化的劳动环境,不断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与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并最终达成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解。
参考文献:
[1]罗闻.技术哲学视阈下虚拟主播具身传播研究[J].科技传播,2022,14(05):131-133.
[2]王晶莹.平台资本与粉丝角力下的虚拟主播关系劳动异化[J].青年记者,2024(01):92-97.
[3]张航瑞.颜值即正义?虚拟场域中的颜值消费[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06):124-137+176.
[4]段永杰,张元媛.数字劳动视域下青年残障播主的平台叙事、符号建构与资本异化[J].残疾人研究,2024(03):54-66.
[5][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8,54.
[6]张振铎,国佳宁,李豪,等.挑战还是阻断?平台算法压力对数字零工主动服务行为的影响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24,32(11):1768-1785.
[7]朱春艳,韩佳宁.马克思生产理论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的四重控制及其批判[J].学术探索,2024(02):90-9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3.
[9][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0,59.
[10]蒋淑媛,张唯肖.粉丝情感劳动的异化逻辑和伦理重塑[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22(06):35-44.
本文系2022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研究”(编号AHSKQ2022D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