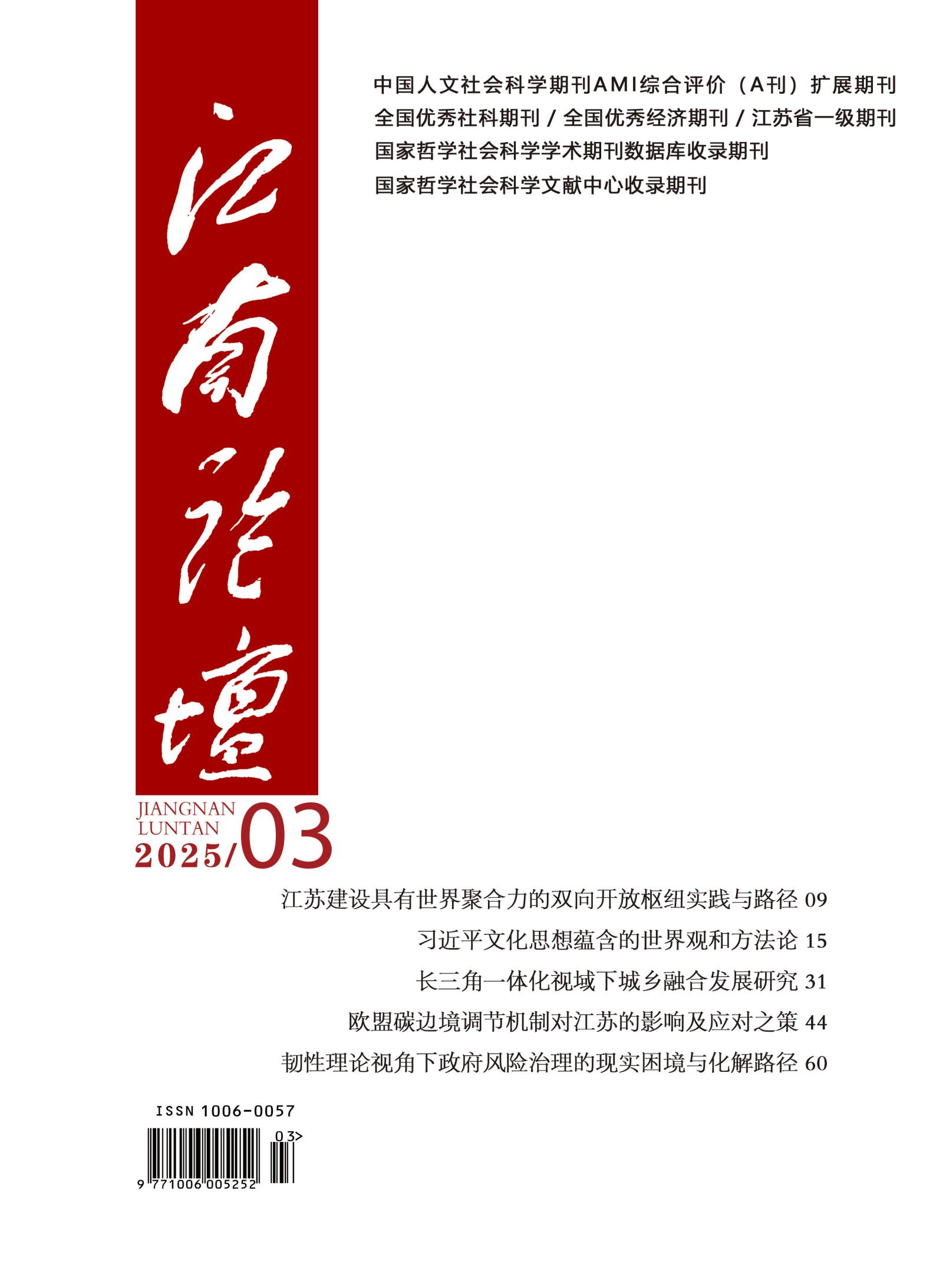刑事审判适用民族习惯法的解释论路径
摘 要 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审判应当通过从立法论到解释论的路径转换适用民族习惯法。在立法论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适用制度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导致这一制度未能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中得到落实,间接压缩了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审判适用民族习惯法的法律空间。相反,解释论路径以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保护理论以及责任主义原理为理论依据,不需要修改相关法律条文,也无须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关于刑法适用的变通或补充规定,就能化解民族习惯法的适用难题。不过,为了确保民族习惯法能够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审判中得以顺利适用,解释论路径还需要程序法的相应配套跟进。为此,要探索建立民族习惯法调查识别机制,将民族习惯法纳入酌定不起诉的考量因素,构建少数民族人民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工作机制。
关键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民族习惯法;立法论;解释论;程序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90条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变通适用制度。由于该条款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导致该条款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立法工作中基本得不到适用。基于此,对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审判适用民族习惯法的立法论路径进行反思性检讨,探索并论证一条具体可行的解释论路径,不仅可以丰富我国《刑法》基本理论,也能够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司法实践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
一、刑事审判适用民族习惯法立法论路径的反思性检讨
所谓立法论路径,源于《刑法》第90条的规定,即“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然而,迄今为止,我国立法实践中尚未出现适用《刑法》第90条制定变通规定的立法例。针对这个问题,绝大部分的学者主张从立法论层面修改相关法律条文的途径来解决。实际上,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变通适用制度在立法实践中适用率低的问题,并不是《刑法》第90条的缺陷导致的,而是由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适用制度的法律地位所决定。具体而言,是宪法法律保留原则限制了《刑法》第90条的适用。
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关于犯罪和刑罚事项的专属立法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62条,“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还有权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根据我国宪法法律保留原则,关于犯罪和刑罚事项的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专属立法权,具有绝对保留的特点。换言之,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的任何机关都无权制定或者修改《刑法》。
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无权批准或授权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从授权立法的角度分析,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9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授权立法,但具有三个限制条件:(1)授权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2)被授权机关限于国务院;(3)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不得授权立法。从《立法法》第9条的表述看,可以直接得出结论:有关犯罪和刑罚的事项,既然《立法法》明确禁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进行立法(行政法规),那么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立法(地方性法规)也必然受到禁止。
第三,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与宪法相抵触。宪法是最高法规范,在法律秩序中具有最强的形式性效力,亦即宪法为法律秩序位阶结构的顶点。[1]显然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也可以从《立法法》第87条找到法律支撑。《立法法》第87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在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情况下,制定关于刑法适用的变通或补充规定。《立法法》第8条规定,关于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换言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无权制定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定。
二、刑事审判适用民族习惯法解释论路径的正当性证成
在立法论路径行不通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无法在刑事审判中根据具体案件的特点适用民族习惯法。事实上,即使不修改相关法律条文,民族习惯法也能在刑事审判中得到适用。从解释论的路径分析,在刑事审判中适用民族习惯法,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基础。
(一)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排斥一切民族习惯法
最早提出罪刑法定原则的刑事古典学派,强调罪刑法定原则的绝对性,主张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2]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建立在刑法内容的完整性、条文逻辑完美性和假设的封闭性之上,在诞生之初对于反抗封建刑法的“罪刑擅断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假设在逻辑上并不可靠。随着近现代刑法理论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发现绝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不足,绝对罪刑法定原则不断受到质疑和变通。正是这种认识的深化,推动了罪刑法定原则本身的发展演变,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软化”。一般认为,相对罪刑法定原则排斥习惯法,但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习惯法。亦即,罪刑法定原则发展至今,一方面排斥入罪加刑的习惯法,另一方面却允许适用出罪减刑的习惯法。正如约尔登教授所言,自由民主式的思维不会接受“以习惯法入罪”的做法。[3]换言之,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解释犯罪构成要件时,可以考虑有利于行为人的民族习惯法,当行为人以民族习惯法为根据实施行为时,可以行为人缺乏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为由,排除犯罪的成立。
(二)法益保护理论为民族习惯法的刑法适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法益保护理论,认定犯罪必须以法益保护为指导,而不能按照风俗习惯的标准认定犯罪。本来,在民族自治地方,民族习惯法最能体现少数民族的社情民意,但民族习惯法毕竟形成于社会生活简单、价值单一的时代,而且民族习惯法往往缺乏明确表达,难以被归纳为一套可以参照适用的规则。民族习惯法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民族习惯法难以作为入罪的依据。但不可否认,民族习惯法在刑法解释层面却能为法益侵害的判断提供一定的依据,特别是在特定的少数民族地区,部分约定俗成的行为虽然形式上具有违法性,但缺乏法益侵害性,对于这部分行为,刑法不宜将其认定为犯罪。在我国当前语境下,如果将这些行为认定为犯罪,显然会受到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既无法让刑法得到有效贯彻实施,也不利于维持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4]基于法益欠缺阻却违法的理论,能够为民族习惯法中的部分行为提供出罪依据。刑法上的不法行为是指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的行为,换言之,实践中存在行为在符合构成要件的同时却缺乏违法性的情况。这种行为因为有了阻却违法成立的原因,其本身就失去了违法性,失去了违法性并不意味着该行为就成为了合法行为,只是具有特定原因的情况下,原本违法的行为不再违法了。[5]
(三)责任主义原理为民族习惯法的刑事责任划定了归责范围
责任主义原理的经典表述为:“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根据责任主义原理,只有当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与结果具有责任能力以及故意、过失、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时,才能对行为人进行非难。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我国西部地区有的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风俗等方面的原因,形成了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的民族习惯。按照《刑法》第258条的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构成重婚罪。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的情形显然符合重婚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如果将这种行为以重婚罪论处,必然违反相关少数民族的民族习惯;若不将这种行为认定为重婚罪,则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根据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犯罪是指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违法且有责的行为。首先,基于罪刑法定原理,要科以刑罚,该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犯罪的类型”。这种犯罪的类型,称之为“构成要件”。其次,根据侵害原理的要求,成为刑罚对象的行为,必须是有害于社会,且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这种为法律所禁止的情况,称之为“违法性”。最后,基于责任主义原理的要求,若对于该行为不具有非难行为人的理由,也不能科以刑罚。这种非难行为人的理由,称之为“有责性”。[6]根据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我国西部地区有的少数民族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行为虽然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但行为人缺乏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即该民族自古以来就实行这样的婚姻习俗,在该民族内部人们都觉得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根本意识不到该行为构成犯罪。言下之意,刑法对于该行为不具有非难行为人的理由,不能科以刑罚。
三、刑事审判通过解释论路径适用民族习惯法的体系性探索
通过从法理到规范的正当性论证可以证明,与立法论路径相比,解释论路径不但与刑法的现行规定相一致,而且与主流刑法理论相契合,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一)实体法:从定罪到量刑
鉴于民族习惯法通常缺乏明确表达,而且只适用于特定少数民族内部,人们难以据此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和法律后果。因此,民族习惯法作为刑法的一般性渊源已不可能,但在刑法适用层面,民族习惯法对刑法适用具有解释功能。
1.民族习惯法影响保护法益的判断。民族习惯法对定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保护法益的判断上。成立犯罪有许多前提,除了罪刑法定主义、罪责原则之外,现代刑法学说还强调行为人必须侵害法益。保护法益对于判断行为的结果要素(法益实害与法益危险)、行为内容(制造法不容许的法益风险)、违法性判断(法益权衡)以及有责性判断(积极侵害法益还是不遵守保护法益的社会规范)等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甚至可以说,倘若缺乏法益概念,刑法释义学的关键操作机制必然面临重大困扰。虽然对刑法学而言,法益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关涉法益的原始提问:如何判断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仍然缺乏清楚的解答。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保护法益提出了不同的判断标准,但绝大多数的刑法学者均一致性地反对将道德伦理和社会风俗当作刑法的保护法益。换言之,刑法禁止将单纯违反道德伦理和社会风俗的行为认定为刑事犯罪。
2.民族习惯法影响刑事不法的判断。在司法实践中,民族习惯法影响刑事不法的判断。根据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犯罪的成立要件包括三个阶层: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其中第一、第二阶层又合称为不法要件,第三阶层又称为责任要件。一般认为,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大体上属于一种类型性的判断。正如黄荣坚教授所言:“构成要件属于类型性、抽象性的判断,而违法性属于具体性、实质性、个别性之判断,亦即三阶层犯罪结构里的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只是初步推定行为的违法性,但并不保证行为的违法性,唯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并且欠缺阻却违法事由的时候,才能确定其行为违法。”[7]以洛朱它西携带藏刀抢劫一案为例,被告人洛朱它西辩解,随身携带藏刀系民族习惯,在抢夺中没有使用,不应认定为抢劫罪。然而,根据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6)川0107刑初40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洛朱它西抢夺过程中携带凶器,其行为已经构成抢劫罪。在上述案例中,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值得商榷。不能机械地理解“携带凶器抢夺”,必须联系该条款的立法目的进行适用。有学者指出:“如果行为人随身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以外的其他器械抢夺,但却有证据证明不是为了实施犯罪准备的,不应以抢劫罪定罪。”[8]在洛朱它西一案中,洛朱它西携带刀具乃是基于藏族民族习惯传统,其携带的藏刀不在国家禁止携带的凶器之列。[9]根据罪刑法定主义“不排斥有利于被告人的习惯法”的规则,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族习惯法为依据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认定为抢夺罪而不是抢劫罪。
3.作为量刑情节的民族习惯法。在已有的案例中,民族习惯法在刑事审判中大多被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例如,在龙光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一案中,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期间,苗族人龙光华依据苗族民族习惯从禄丰县大水沟、大竹山、老火山的山上捕捉了6只不知名字的野生鸟类,拿回家驯养。2019年8月21日,公安民警在龙光华家院内查获笼养野生鸟类6只。经云南濒科委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查获的6只涉案野生动物中,白腹锦鸡1只为国家Ⅱ级保护动物,价值为5000元;白腹隼雕1只为国家Ⅱ级保护动物,价值为5000元;其余白颊噪鹛1只、灰翅噪鹛2只、画眉1只为国家保护的三有动物,价值合计1900元。根据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法院(2019)云2331刑初226号刑事判决书,云南省禄丰县人民法院虽然认定龙光华罪名成立,但考虑到苗族民族习惯,最终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宣告缓刑二年。量刑情节是反映罪行轻重以及行为人的再犯罪可能性大小,从而影响刑罚轻重的各种情况,是选择法定刑与决定宣告刑的依据。以刑法有无明文规定为标准,可以将量刑情节分为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民族习惯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在刑事审判中予以考虑。上述案例中的民族习惯即属于典型的酌定量刑情节。民族习惯法之所以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理由正如上文所述,民族习惯法能够影响不法的判断,也能够影响责任的轻重,可以说明预防必要性的大小等。
(二)程序法:从起诉到审判
为了确保民族习惯法能够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审判中得以适用,还需要重视程序法路径的保障作用。有学者提出,为适应刑法在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施行的现实需要,可以通过程序法制度设计得以实现。立法论路径是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工程,涉及刑法亲告罪的修改、刑事诉讼法自诉案件范围的修正、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变更等。事实上,关于民族习惯法的适用问题,并不需要修改大量法律条文,在解释论层面也可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1.探索建立民族习惯法调查识别机制。亚里士多德认为,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实际上比成文法还更有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为重要。民族习惯法是人类长期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套行为规范,它源于各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鉴于民族习惯法的不成文特征,要在刑事审判中顺利适用民族习惯法,首要任务是建立民族习惯法调查识别机制。“各个地方应以本地方民族为单位,加强对习惯法的归类整理,由该地方权力机关规范统一的习惯法类型和判定标准”。[10]同时,还要加强民族习惯法的立法转化工作。例如,西藏自治区针对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问题制定《西藏自治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就“赔命金”问题出台《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赔命金”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针对少数民族的结婚问题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补充规定》等。另外,应当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民族习惯法的调查识别机制,组织法官深入少数民族内部,对民族习惯法进行系统收集,为法官在具体审判实践中适用民族习惯法提供法律基础。
2.将民族习惯法纳入酌定不起诉的考量因素。为了让民族习惯法能够在刑事审判中得以适用,有学者主张,“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基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可免于刑罚处罚的成年人犯罪案件补充进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对侵犯财产犯罪案件和人身伤害犯罪案件,可以根据民族文化传统将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不起诉的附带条件”。[11]然而,这样的主张仅具有理论探讨的空间,绝无实践操作的可能性。首先,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具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为特定适用对象,其目的是帮助、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如果因为民族因素将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成年人,则有违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立法目的。如此,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其次,如果少数民族犯罪嫌疑人属于未成年人,同时具备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那么自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不需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关于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最后,将民族习惯法纳入酌定不起诉的考量因素,也能让民族习惯法在不起诉程序中得以适用。酌定不起诉,又称相对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可以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一般而言,人民检察院需要考虑的参考要素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犯罪目的和动机、犯罪手段、危害后果、悔罪表现以及一贯表现等。在人民检察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只有在确信不起诉比提起公诉更为有利时,才能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显然,民族习惯法对于少数民族犯罪嫌疑人的上述因素均有重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因素。而且,将民族习惯法纳入酌定不起诉的考量因素,与酌定不起诉的法律规定也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3.构建少数民族人民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工作机制。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审判中,还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大部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行为人更愿意接受民族内部有一定威信的人的调解,而不是接受判决。民族内部有一定威信的人参与到案件中去,对于认罪认罚、改过悔罪以及积极赔偿被害人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法院在审理彝族民事案件时,根据彝族“德古”调解的民族传统,特邀彝族“德古”作为民族人民陪审员参与司法调解,这不但有利于彻底解决当事人的民事纠纷,而且有利于在彝族聚居地区普及基本法律知识,为法院的审判工作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首先,聘请少数民族居民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人民陪审员法》)的规定并不冲突。只要少数民族居民符合《人民陪审员法》第5条规定的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条件,并且没有担任人民陪审员的禁止事由,那么人民法院聘请少数民族居民参与刑事审判就具有法律依据。其次,非少数民族法官在审理涉及少数民族居民的刑事案件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考虑民族习惯要素,如果法官不熟悉民族习惯法,将无法做到法律与习惯相结合,让判决结果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少数民族人民陪审员的加入,对于解决这一难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后,从程序法的角度分析,刑事定罪以“排除合理怀疑”为证明标准,判断是否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恰恰需要与行为人具有同样生活背景和民族风俗习惯的少数民族人民陪审员根据生活经验进行判断。这对于减少甚至避免少数民族的刑事错案、冤案,具有普通的人民陪审员无法比拟的优势。
综上所述,由于《刑法》第90条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适用制度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所以,主张让民族习惯法在刑事审判中得以适用的立法论路径,欠缺合理性与可行性。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保护理论以及责任主义原理为解释论路径提供了法理依据,不需要修改相关法律条文,也无需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关于刑法适用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的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违法性判断理论、有责性判断理论自有民族习惯法的适用空间。同时,为了确保民族习惯法能够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审判中得以顺利适用,还需要重视程序法的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日]芦部信喜.宪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2][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
[3]梁根林,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9.
[4]苏永生.刑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动关系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1.
[5][日]泷川幸辰.犯罪论序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5.
[6][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32.
[7]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21.
[8]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79.
[9]傅亚光.奇特的藏刀[J].文史杂志,1996(03):52.
[10]周世中.民族习惯法在西南民族地区司法审判中的适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64.
[11]刘之雄.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施行刑法的路径转换——从实体法到程序法[J].法商研究,2017,34(02):38-44.
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宗教习惯法研究”(编号23SKJD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成都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