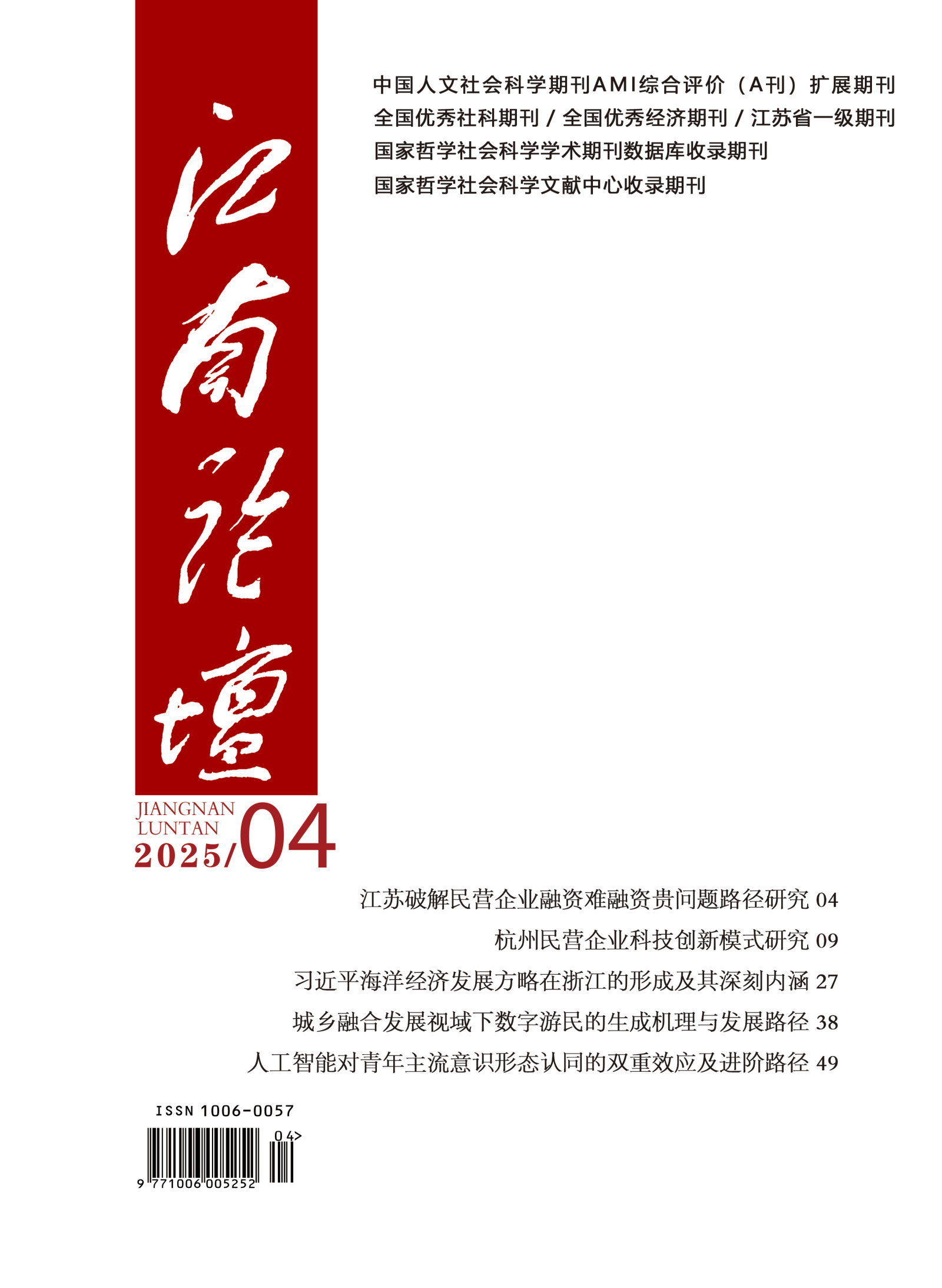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摘 要 全球化使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引发了世界性的危机。面对这种状况,中国审时度势,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追溯“共同体”的缘起,东西方文化有着共同的美好愿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从哈氏交往理性视角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探析交往行为理论,对于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有启发。应促进彼此承认,开展平等友好协商;广泛凝聚共识,构建合理国际秩序;多方共同发力,消解西方话语霸权。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
全球化的形成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全球化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了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引发了全球性的危机,资源、环境、人口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面对世界性的难题,单个国家独木难支,需要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衷共济,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基于此,中国适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团结世界各国,共同守卫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面对世界范围的冲突和争端,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他认为:“我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3]哈氏的这一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出极强的关联性,探析“交往行为理论”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缘起
人类社会自诞生之日起便是以集体的形式存在的。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共同体”概念在早期东西方文化中均有提及。
(一)西方视域下的“共同体”
“共同体”在古希腊被表述为“Koinonia”,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亲密关系及其表现。“Koinonia”多次出现在《圣经》之中。在中世纪,“共同体”与“团契”的意义更为相近,意指教徒之间的团结、友爱。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确立使得交往的范围空前扩大,世界自此真正连为一体,“共同体”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卢梭提出“主权在民”思想,旨在通过对话协商的形式体现“共同体”的意志,构建和谐自由的契约共同体。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先前哲学家们关于“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共同体”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形成了为了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结合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将“共同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尚未摆脱人的依赖”的封建社会共同体,“尚未摆脱物的依赖”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当前的全球化具有“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特质,各国之间的交往以“资本”为中心,是一场恃强欺弱的零和博弈。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交往是造成全球危机的根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超越,将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带领世界人民走出困境。
(二)东方视域下的“共同体”
中国古人一直追求建立美好和谐的大同世界,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安居乐业。中国古代的共同体思想源于儒家对于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和弘义融利的价值导向。《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想要构建一个人人有德、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无人不保暖、无处不均匀的和谐社会,实现世界大同。这些思想蕴含着迄今为止全人类所追求的共同价值——和谐。如果说二圣孔孟勾画了理想社会的蓝图,那么继孔孟之后的荀子便开创了通向大同世界的途径——义利兼顾的“务实王道”。荀子的义利观对我国的外交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弘义融利是我国开展外交工作的价值导向,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的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发表了题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的重要演讲,指出:“中巴要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成功构建是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开端,这表明中国所要构建的共同体是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共同繁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家对于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和义利兼顾的价值导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并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义利兼顾的价值导向,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的大同世界理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4]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国人民对“人类将怎样实现发展,人类将走向何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二、交往行为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契合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哈贝马斯对于交往的阐释和推崇同我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所践行的外交理念不谋而合。然而,交往行为弱化了劳动的作用,将交往过度拔高,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和幻想色彩。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克服了哈氏理论的缺陷,顺应时代潮流,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实现了对交往行为理论的超越。
(一)交往行为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性
以个人理性和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全球秩序观导致全球治理频频出现危机。面对旧秩序观的失效,中国适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全球治理观,旨在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在政治上,我国主张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安全上,我国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在经济上,我国倡导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在文化上,我国主张促进文明交流,加强文明互鉴;在生态上,我国提倡各国同心协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五个方面的构建都离不开平等基础上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
交往行为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先依据行为者与世界的关系比较分析了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以及戏剧行为,然后将交往行为引入其中,实现了对上述三种行为的综合和超越。目的行为即工具性行为,是指行为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利用工具介入客观世界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受到群体共同价值的约束,遵守群体共同规范的行为;戏剧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将参与互动的社会成员看作自己的观众,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为;交往行为是多个具有表达能力的行为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成行为主体间共识的行为。
哈贝马斯通过对上述四类社会行为的阐述和比较廓清了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概念——交往行为。从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来看,目的行为涉及真实性,规范调节行为涉及正当性,戏剧行为涉及真诚性,而交往行为同时涉及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从行为协调机制来看,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都是通过“影响”来调节行为的,唯有交往行为是通过“同意”来调节行为的。相较于其他三种行为单方面地关联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交往行为同时涉及了这三个世界,是其他三种行为的综合和超越。因此,从现实性的角度来看,只有交往行为才是同时满足三种有效性要求的合理行为,只有交往行为才能够使人们挣脱“物的异化”,带领人们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行为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相关,从哈氏西式的语境来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西方国家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言语和文化背景上的便利,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实践和超越
哈贝马斯意图通过交往理性来为现代社会重建理性基础,以挣脱现代性的“牢笼”,但他的理论过于理想化。“哈贝马斯脱离开生产关系革命、异化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而苦心经营的所谓‘交往合理化’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和美好奢望”。[5]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交往行为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孳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交往行为理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理论性和现实性上实现了对交往行为理论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越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在科学判断21世纪世界大势的基础上回答“世界走向何方”的智慧结晶。面对当前的全球性问题,中国在各个领域为问题的解决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腾飞为世界的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活力,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使发展惠及周边各国、惠及世界。在生态上,中国高度重视环保工作,人工造林面积长期居于世界首位,其“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塞罕坝、库布齐沙漠绿化”等工程的成功实施,切实改善了生态环境,有效遏制了全球变暖的趋势。此外,中国在政治、文化、安全等领域都将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付诸实践,为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交往行为理论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相关,但其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究其根源在于哈贝马斯片面夸大了交往的作用,未能看到劳动在实现人的解放过程中的根本性的作用。正如基恩所言:哈贝马斯“关于马克思的劳动范畴的描述,很不完整——实际上是片面的。”[6]哈贝马斯只看到了劳动工具理性的一面,却未能看到劳动在摆脱其异化形式之后对人的解放性的一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在理论性上实现了对交往行为理论的超越。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坚定的执行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心。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与西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生态不同,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凝聚世界共识,立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擘画了人类文明的宏伟蓝图,指引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三、交往行为理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固然带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但哈氏对交往的独到理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在现实世界里,行为主体间很难达成理想的交往,但哈贝马斯“乌托邦”式的假设将“理想交往”的特征、条件抽取出来,并将其理论化,为达成“理想交往”找到了可能。交往行为理论对当前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启示有以下三点:
(一)促进彼此承认,开展平等友好协商
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性的存在是承认产生的基础。相互承认是这样一种理解:自我和他者的生存需要依靠双方的共存来实现。相互承认这样一种意识:如果双方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话,自我和他者都是必须”。[7]“夫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羹汤之所以美味,在于调和了各种不同的食材。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诞生了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只有承认彼此才能开展交往、实现共存。
然而,在现实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大多是工具理性宰制的交往,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交往。在工具理性宰制的交往活动中,行为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将对方视为客体,是主客体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是难以达成共识的,其结果往往是强者对弱者的霸凌。西方国家的交往活动是典型的工具理性宰制的交往活动,是“以资本为中心”的交往活动。在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交往过程中,他们更多是将其他国家视作可以攫取利益的客体任意宰制,并未将其纳入同等的主体地位进行考量。一些国家的发展史不啻于一部对其他国家的掠夺史,在这一过程中,这种“交往活动”致使国际社会冲突频频,不断累积的矛盾难以消解最终得以激化,屡次将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面对当前不合理的状况,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各国承认彼此的存在,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交流,在友好的协商中达成共识,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二)广泛凝聚共识,构建合理国际秩序
在现实生活中,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会导致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难以达成共识,产生矛盾甚至爆发冲突。当主体间的利益不可调和的时候,倘若没有合理的秩序规制,双方便会采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强者依靠暴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压制弱者,但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局面。如何避免这种冲突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这就需要制定一个共同的规范来约束彼此。这个规范必须是“合理的”,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规范必须建立在主体之间达成的共识基础上,只有在主体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借助语言的中介才能够产生。哈氏的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拨乱反正,旨在构筑一个达成多方共识的、“合理的”国际秩序。
现有的国际秩序正处于新旧更替的过渡阶段。一方面,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难以应对当前全球性的危机,世界范围内冲突不断。俄乌战争的胶着、巴以冲突的升级无不预示着战争的硝烟已经再次笼罩在21世纪人类的上空;另一方面,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边秩序在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调停下,纠葛千年的“宿敌”伊朗和沙特成功恢复外交关系,昭示着和平的曙光重新普照于纷争的尘世。
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必须推动构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多边秩序。当前,中国正从多个维度发力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不同的困境,中国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推动构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海洋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针对不同的地域,中国秉持从“小圈”到“大圈”共同发力逐步构建的思路,推动构建了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针对不同的国家,中国坚持弘义融利、友好互助的准则,推动构建了中巴命运共同体、中柬命运共同体、中老命运共同体等,为各国的共同繁荣注入了强大活力。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极大地改善了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
(三)多方共同发力,消解西方话语霸权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集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三个有效性为一体的行为。当前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舆论长期“失范”,这种舆论引导下的交往已经不能称之为“交往”,显然,它并不满足三个有效性要求的任何一项,其中,在“真实性”的缺乏上尤为突出。
一直以来,国际上主流的社交媒体和平台都被西方国家把持着,世界缺乏一个自由发声的平台,西方国家凭借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在国际舆论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借助其国际性的社交平台不断输出西方价值观,对异己力量肆意进行抹黑。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中国为共同发展作出的努力赢得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呼声。
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过程中的各个投资项目,为沿线的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无可辩驳,便又故技重施,打着“人权”“环保”的幌子抹黑中国。面对西方国家的诽谤和污蔑,应坚持多方共同发力,消解西方话语霸权。首先,在社交平台建构上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数字技术优势,推动构建独立于西方的平等、真实、包容、多元的社交平台,倾听世界人民真实的声音。其次,在国际上要让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弱国”发声,代表发展中国家促进全球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共享。再次,针对西方媒体基于谎言和偏见的虚假报道,要立足实际、据理力争,揭开西方媒体的虚伪面具,还事实以真相,让“流言”不攻自破。最后,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讲自己的话,避免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要将中国话语用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出来,让世界人民倾听真实的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18.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3]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J].外国文学评论,2000(01):27-32.
[4]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395-396.
[5]陈雄辉,关锋.交往的乌托邦:哈贝马斯人类解放思想评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130-132+144.
[6][美]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57.
[7][美]诺曼·莱文.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5.
本文系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支持2023年度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课题“‘大思政’视域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的路径研究”(编号2023JG088)和2022年度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一般项目“新时代好青年的培养机制研究”(编号2022SDMY006)的阶段性成果。
(行国通 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雯雯系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马玉】